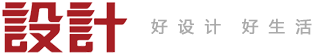從“引進來”到“走出去”、從模仿到創新、從價廉到物美,改革開放這四十年,也是中國制造發展尤為關鍵的四十年。
這期間,我國制造業都發生了哪些改變?工業設計現狀如何?設計教育工作者正在從哪些角度培養人才、布局未來?設計行業現存哪些問題?
于此,蔡軍是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、藝術與科學研究中心設計管理研究所所長與《設計》雜志分享了自己的觀點。

《設計》:我們知道國家正在通過發布政策加強對制造業的扶持力度,比如中國制造2025,請您從行業前沿的角度出發談談近四十年來中國制造的變化。
蔡軍:在改革開放之前,我參與過中國輕工業詞典的編寫,那時候沒有工業設計的概念,寫的是輕工產品造型設計。本質性的變化是真正把制造和設計聯系到一起,是從改革開放四十年開始的。
前期因為我們沒有技術,連洗衣機、電視機等家電生產都是照搬國外的流水線,所以很長時間以來基本上都是以抄襲、模仿或引進為主;之后有一點改變是在90年代初,聯想和海爾都起來了。當時我們帶學生去了一些做小家電的企業參觀,那個時候輕工企業正在轉型,但很多沒有成功。再后來是IT產業的興起幫助了很多企業“站起來”,原因有二,一是民間推動,二是市場需求。
2000年之前學校培養了大量設計專業的學生去公司做展示、裝修、廣告等,但真正在工業設計里發揮作用的是2000年之后的畢業生。之前國內幾乎沒有平臺和渠道,也幾乎沒有企業要工業設計人才。 所以互聯網開始興起的時候,我認為是傳統制造業真正要開始改變的時候。
人工智能、物聯網等概念影響了整個制造業的特點,人口紅利的問題和過去完全不一樣。我們今天看中國制造,是基于一個物聯網數字化,定制化,網絡化,全自動化或者說是信息化的概念去看。設計的手段、技術、方法體系都發生了改變。比如現在做設計必須要了解市場,做用戶研究,包括服務設計和產品設計等,我認為和過去傳統工藝相比更加復雜。
《設計》:那么是否可以說傳統的教學方法或許不太適用了?設計專業的課程設置會有一些變化嗎?
蔡軍:每個學校不一樣。有些走得很靠前,有些很保守,每個學校各有各的特點,或者說在一個學校內部也參差不齊。比如有些老師會意識到這個變化很大,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,以及引進有留學經歷或國際背景的師資去帶動;同時也有一些學校很傳統,只給學生一些傳統的知識結構。
過去傳統的教育可能是把學生培養成一個特別合格的設計師,把所有的技能都掌握到位,這沒錯,但走到現在的話,由于很多企業已經不止滿足于生產,他們都在變化和轉型,所以我們不能只是把學生培養成“工具”,而是具有開拓思維的創造者,戰略思維非常重要。
比如我們現在讓學生去做設計研究、用戶研究等,它會帶來另外一個挑戰,過度側重研究有可能會造成放棄對物質化設計的關注。這個研究過程沒有形態化的概念,而是在做流程,這也是對設計提出的新挑戰。
《設計》:對于企業設計戰略或者設計規劃的發展來說,哪些條件比較重要?
蔡軍:一個企業有幾個基礎的條件要弄清,比如目標市場、技術優勢、人力資源優勢、還有企業使命、企業愿景這幾條都是在管理學中強調得特別多的。
現在設計介入企業最重要的就是設計價值的引入。這是傳統企業并沒有思考的,因為傳統企業相對從制造的角度更關注,比如供應鏈等。其實不是這樣的,因為設計的核心是為消費者和用戶創造更最好的體驗,同時也是在在滿足用戶和企業的利益。
所以我覺得關鍵還是企業如何去認識和轉換對設計價值的認識。設計價值已經不僅是美學價值了,它其實蘊含著商業價值和用戶價值,以及通過設計能夠提升企業的價值鏈的增值,同時還能夠通過設計去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。
《設計》:我們知道今年是中國設計四十年,我國設計行業在這其中也發生了很多變化,您認為未來中國設計將會向怎樣的趨勢發展?還有哪些問題亟需解決?
蔡軍:中國設計四十年,簡單的說,這是一個通過學習國外設計,從引進、吸收、模仿,到開始意識中國制造,或者說設計自信力的恢復過程。
在這中間還有幾個問題沒有解決:
一是對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不夠健全的問題。現在由于很多產品在不斷被抄襲,原創設計既然得不到保護,大家就不敢創新,那么就更不去保護了,這是一個惡性循環,引起了很多的爭議和矛盾。我認為政策上要更改對專利保護設計的定義,重新加大保護力度。這也是貿易戰里面特別大的一個問題。四十年是這么一個過程,有學習模仿,也有批判和揚棄,包括設計本身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重新梳理,都是今天設計正在面臨的局面。
二是設計的系統和研究方法還不夠成熟。我們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,現在需要沉淀下來一些東西,也就是如何發展出自己的研究方法,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問題。需要更多設計師去思考如何整合整體資源,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。比如做產品背后的研究,包括可持續發展、材料回收的問題等等。
三是非遺文化的保護。要想真正地保護非遺,我覺得一個是保留原汁原味,另一個是要有創新,這兩方面的融合要更協調、更有品質,比如我們可以把它演繹到現代生活的一些場景中間去應用,可以通過文化藝術和生活的結合滿足更加多元化的市場需求。
《設計》:明年是包豪斯成立100周年的紀念年,您認為包豪斯對中國產生了哪些影響,未來發展會給中國設計帶來怎樣的變化?
蔡軍:包豪斯最重要的貢獻是起到了一個扭轉觀念的轉折點的作用。從傳統的手工業社會到大工業,它其實是在這個歷史階段轉換了設計這門學科,促進了設計學科的產生,讓設計去適應大工業,同時奠定了當代工業設計的觀念,認可這種工業化的制造、語言和工業化的邏輯形式。
但同時包豪斯也存在它的局限性,比如它有很多激情性的、藝術化的、很感性的東西,包括很多先鋒派藝術的風格,這些思想后來與大工業的產業邏輯是有沖突的。一味把包豪斯放到現在的中國來強調,不適應現在已經進入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局面,所以我并不贊同。烏爾姆的設計理念從現代意義上來說遠大于包豪斯,應該把包豪斯和烏爾姆放在客觀的角度并列起來去看,去認識。
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主體、技術創新的主戰場,其實力和技術水平體現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。
改革開放40年來,中國創新投入不斷增加。1978年,我國研發經費支出為52.89億元;2017年上升為1.75萬億元,居世界第二位,占GDP比重達2.12%,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。但與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相比,我國設計的發展之路仍然任重道遠。在設計走向獨立、走向成熟的過程中,更是離不開優秀的設計教育工作者。我們希望未來“中國制造”的標識能夠成為一個愈加鮮明的中國符號。